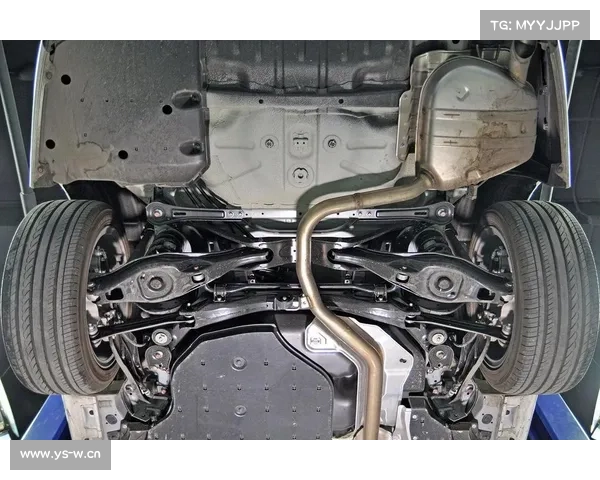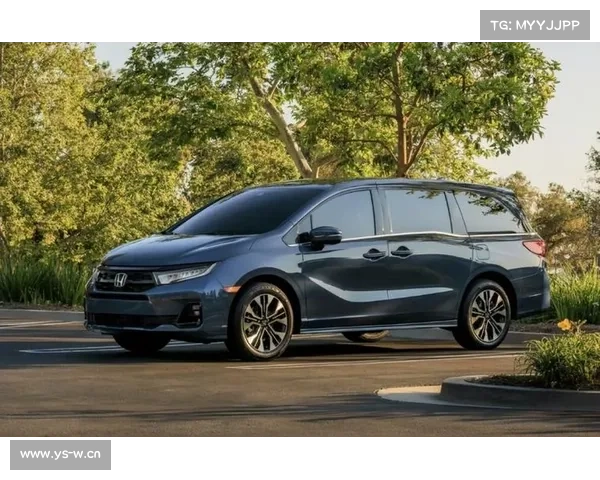长安人多。百宝街上总是一阵阵嚷嚷的动静,没人会在早市开铺时说半句话。那天街口又热闹,吆喝声起,有卖胡饼的、有卖绣履的,全都摊子小,心气高。街最东头,靠近胭脂铺的转角,蹲着个青年,叫阿福。他的摊子不起眼,就几块板儿,摆满木疙瘩和梳子。头顶那面写歪了的招牌,像谁写来糊弄小官差,倒怪扎眼!

阿福不是本地人。小时候,家底薄,父亲靠两把斧头过日子。父亲走得早,那年冬天米价暴涨,棉衣都卖了换米,阿福一个人蹲炕头发呆。他懂事得有点晚,家当散了大半才明白,没有把子力气撑不起家啊?有人说他软弱,谁知道夜里他悄悄去工地揽活,用破毡子裹着睡。从不开口喊苦,没人把他当回事。
好多年阿福什么活儿都干过,剃头、补鞋、当过脚夫。不过不是所有事都做得成,有空他总琢磨点稀奇木活,脑子也明白。可惜,初时做出来的东西丑得厉害,没人肯买。他脸皮厚,摊也不开,只在茶肆寄卖。头一年赔了个底掉,连饭钱都倒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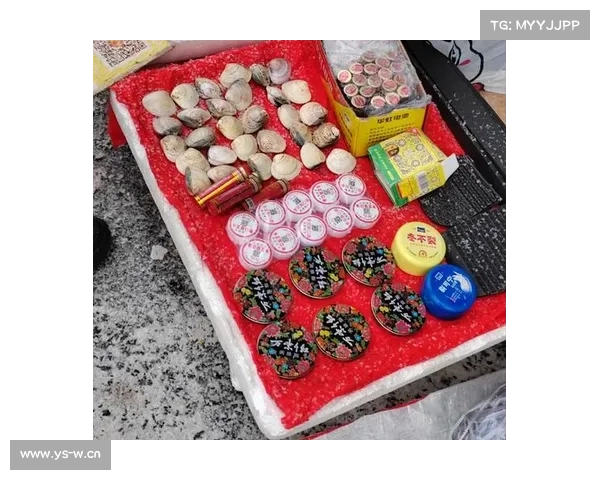
阿福后来不死心,还是选择自己出摊。他觉得,得让人看见,才有可能成交。百宝街选址,不全靠眼光,多少还要点运气。人流多,混个脸熟,东西卖得出去的希望大点。最初铺子空空,只几样小瓶、木叉、木梳。这些全是他熬夜做的,手指枯瘦,指甲里常年干着木屑。问价的人多,真买的却寥寥无几。
阿福的谋生路子很怪。他不爱跟同行聊天,反倒约些路人问东问西。瞧见妇人头发长,他收了心思,雕新样的梳子;见老翁牙口不好,试做木碗浅底短沿,方便端拿。别人笑他腆着脸拉生意,“穷酸气”,他偏不在意。有人觉得他滑头,敢给主顾闲扯半天才送东西,啰嗦得很。可就是因为啰嗦,有几个主顾反复过来。一来二去,起了微妙的信任。说不清为什么,买他的木盘,多数是街角茶摊、豆花婆姨。

其实这些年,市面上的木活儿不稀罕。有人做得精巧,有人求个便宜。阿福的东西不算最好,但有个讲究——样样有改良。譬如木梳,齿间顺滑不刮头皮;做饭用的勺,柄略弯,放案上不滚烫。他不是一味迎合,有些顾客提议太奇葩,他也懒得做。手艺有时要固执些,这么说对么?
百宝街不是个安稳地方,时常闹点小乱子。恶霸李霸天在街口横着走,动不动就要收钱,他惯会看人脸色挑软柿子捏。阿福摊子拢不住钱,最怕这类人盯上。谁都说,李霸天欺软怕硬,是市井的毒疮。阿福曾见他收钱时,摊主眼里只有忍气吞声——人微言轻,谁肯管闲事?

李霸天的算盘打到阿福头上。开口就要保护费,价格定得死高。阿福正愁应对,背地找了几个旧友商量。他胆子不算大,这次却做得决绝。他甚至一度踌躇过,要不要低头?有失体面,可留青山在?可他咬牙坚持不认,咱不能纵着他们吧!
两天后,阿福去县衙报了案。官差平日管事不多,这次却行动了。李霸天得风声,气急败坏地来闹场。阿福预先布了个小机关,就地挖了坑,藏了机括。大冷天,他用草绳障眼,等着他们自投罗网。案犯进坑那一刻,围观的不啃声,就听老街那头的铜铃一阵乱响。

衙役们随后赶到,将李霸天团团围住。一场腥风作雨,意外就此止息。有看热闹的嘀咕说,阿福蛮横,敢以身犯险。有人反唇相讥,这才叫有骨气!其实哪有什么英雄,不过是命绝路才出此下策。过后好长一段日子,街坊都议论纷纷,“小木匠阿福把李霸天撂倒了!”
事后阿福悄无声息。木梳、木碗销量翻番,不少人特意来买,也有讲究品头论足的酸秀才来凑热闹。有人指责不厚道,说阿福“沽名钓誉”,其实买卖归买卖,谁真在意这些?摊前总有几个孩子嘻哈玩闹,闻着木香,翻弄新鲜小玩意儿。生意未必最好,但他的摊前气氛怡然,像家常院落。更多人愿来,愿意多聊几句。

阿福干活越发专心。样样木器又增花样,有时夜里灯火通明,一刻不停。他开始雇人帮忙,有两个学徒跟着打杂。街坊羡慕,阿福却嘴上谦虚,这都是街上的福气。也不全是。他心里盘算着再扩张,取院借地,一点点大起来。
有人觉得他忘本。他成了新的“摊主代表”,什么事都插一脚,甚至被说“跋扈”。这诡异吗?也许。但阿福还是那个阿福,也会失眠,怕哪天自己撑不起摊位。长安城的风最喜欢把新招牌吹倒,谁都看不清以后。
加拿大预测
慢慢地,木工坊成了行会。从前孤身一人,如今有十几把斧头锯子。阿福担心旧手艺被淘汰,专门开了夜学,教穷孩子做木工。有人说他图名,也有人说他眼光长远,但总有新的师徒愿意拜他门下。他不怎么应酬,更多时间泡在作坊里。时不时盯旧物新样,反复琢磨,似乎怕一步错满盘皆输。
这些年长安变得更快。百宝街的小摊紫气东来,官道拓宽,生意越做越大。木器也出了新款,有的走高端,有的主打实用。阿福有点迷茫,自己浮沉数年,难道真的靠幸运走到现在?细想好像也不是,只是熬过一段又一段的苦日子罢了。有时幸运很荒谬,苦难的积淀让人分不清到底谁是“聪明”,谁只是硬扛到天亮?

也有人说阿福性子软。若当年他早早放弃,该不会有这些风波吧?可有时候,硬气和委屈全都在一念之间,谁又说得清?
**哪个阿福才是真的阿福?买卖人、手工匠、百宝街的英雄,没人给出确切答案。**

历史里从来没有绝对的对错,什么木碗木梳,都不过是一腔执拗和点子积攒出的小把戏。阿福没多大志气,也没闹腾出翻天动地的大事。可百宝街今日看热闹、明日论是非,一个适合自己的小摊,有人买账就够了。
**就这样,阿福的故事继续,木器继续传开,他还是每天戴着旧帽子,早起出摊,偶尔想起要“守住本心”,再多想几分又觉得太俗气。**